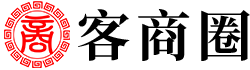没有出色的学历背景、没有父母支持、独自“北漂”……在26岁的尴尬年纪,换作是你,你会怎么面对生活?
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女主人公川尻松子就拿到了这样的人物设定。
但不同于普通人升级打怪的常规剧情,看似一无所长的川尻松子,愣是将自己的人生玩成了不含任何主角光环的逆天模式。
给自己倒上一杯轩尼诗,再倒在舒适的沙发里,一边浅酌,一边欣赏着余额“可以造一幢大楼”的存折——
这并不是什么高级白领的精致人生。
恰恰相反,在喝完杯中物后,开始准备上班的主人公,目的地是一间被称为“白夜”的风俗会所。

在初入行的第三天,她拿到手里的薪水就高达七万日元。
一个风俗业从业者,凭什么能拿到如此高的报酬?
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日本社会派大师山田宗树的本意其实并非架空批判。
在日本,这样令人想入非非的风俗业里,多得是你不知道的秘密……
在禁令中蓬勃生长的风俗业
既然有横财,那为什么不赚?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风俗从业者的心态,趋利,无疑是她们选择入行的第一诱因。
据调查,日本的风俗从业者,大部分都是良家妇女。
与刻板印象中的情色交易不同,在客人面前游刃有余的风俗女,人后的模样却规整的过分。
甚至,构成这部分灰色产业的主力军,还是那些涉世未深、正在忙着与老师和考试“交战”的在校女学生。

这个意料之外的事实,也许会让你自作主张,为她们设想一个饥寒交迫的穷苦出身:
既然风俗业在日本如此风靡,肯定是政府授意,强行逼迫女性入行从业的。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从奈良时期到如今,由性产业禁止国流变为性产业规制国的日本,每一步都在试图控制国民滑向欲望的深渊。
但很显然,日本的政府官员们,还是大大低估了在长期色情产业浸泡下野蛮成长起来的本国国民。
奈良时期,日本繁华要道或官营驿站内,就已经出现专门经营卖春业的“长者”;而到了平安中期,这部分“长者”家中也开始置有“专门女性”,用来给客人提供服务。
这,就是日本风俗业的最初雏形。
在接下来的室町、江户时期,由于政府的有力推动,卖春女们巧立名目,摇身一变成“公娼”,不仅有了合法的“职业证明”,还能在前者默认的红灯区内,心安理得开门迎客。

这一时期,没有受到政府统一管理的“私娼”,就好比是街边大排档:相对自由,但并未得到保护。
站在政府的角度,“保护公娼、取缔私娼”的做法,虽然不可避免地扩大了民众的欲望心理,但也对奈良时期不加管制的风俗业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所谓的红灯区,更像是给民众在理智与欲望间划下了一道屏障:喝酒可以,但不要贪杯。
按照这样的分工逻辑,日本的色情业,本可以与其他行业同时存在,相安无事地完成着自己被赋予的使命。
但,二战后深受美国影响的日本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风。
1946年,日本发布《公娼制度废除之依命通达》,正式对公娼实行禁止条例,并宣布“解放娼妓、艺伎”,以维护人权,清正社会环境。
风俗色情勾人欲望,既影响民众贡献经济生产力,对从业者本身也有人权侮辱,取缔了不正皆大欢喜?
照着这样的想法,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对风俗行业的禁令是一条接着一条的下发,试图彻底整改风俗行业。
然而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所谓的“禁令”,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还遭到了反噬——
因为不满政府法令,风俗从业者们联合起来,从“地上”转到了“地下”,管控难度直线上升。

原因很简单。
明治时期恰逢战乱年代,普通民众生活得非常困难,失业、少食,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选择从妓是女性不会出错的最优解。
更何况,日本政府的禁令,看起来也并不公平。
为了安抚驻军,名义上保护女性的日本政府,开设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以招聘“女事务员”的借口来募集风俗从业者。
这样的双标对待,惹怒了以风俗为业的人们。
特别是在战后《风俗营业取缔法》的出台下,与政府试图转型成为“性产业禁止国”相对的,是其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民众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只得出面与风俗行业完成洽谈,共同制定《卖春防治法》,结束了这场争执。
在这份法案中,政府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将风俗从业者的正当行为,规范在了“非实质性操作”以下的大面积空间内。
靠着这股灰色产业的东风,日本的风俗行业反倒更加顺风顺水地发展了起来。
自此以后,日本政府与风俗行业的“博弈”似乎也进入了无限循环模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死板的政策更厉害的是灵活的方案变动。

甚至,连风俗行业的从业人数也来了次规模颇大的飞升。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为政府正名:日本风俗业发达,确实不是政府监管无能的锅。
那么,既然不是政府授意,那为什么连家庭主妇、在校学生都变成了风俗行业的主力军?
为什么女学生、家庭主妇反成风俗从业主力军?
在日本,风俗行业有着不成文的划分规则。
根据服务程度的不同,从上至下,日本风俗行业大致可划分为艺伎、舞伎、歌舞伎三种。
据日本官方发布的“外国游客行动特性调查”,号称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红灯区的新宿一带,成为了最受游客喜爱的游玩地区。
而那一带自成一派的标志性建筑物,当属歌舞伎町无疑。
1923年开始,孕育了江户平民文化的新宿下町地区便频繁遭受天灾人祸,繁荣程度大不如前。
为了弥补这一地区民众娱乐设施的相对缺乏,日本政府出面设立歌舞伎町,试图“建成以娱乐为中心的大面积商业地区”。
以歌舞伎的表演活动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日本政府的初衷无疑是健康的,下町地区也曾因高效的建设工作而被媒体称为“全首都复兴的桂冠”。
但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最终建成的歌舞伎町,并没有成为可供艺术性歌舞伎表演的大型场所。
恰恰相反,在民间各方有意无意的推动下,新宿下町,反而成为了花街与妓场的聚集之地。

意识到这一点时,即使政府有意整改,但面对“白天经商 夜晚销金”的流氓商家,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由此,作为“卖艺不卖身”的风俗行业,聚集在新宿的歌舞伎町,逐渐发展出一种利润颇高的陪酒文化。
被称为“日本第一陪酒女”的爱泽艾米丽就曾在采访中表示,即使作为滴酒不沾的过敏性体质,她的收入月流水也达到了 1 亿 5 千万日元。
哪怕是风华不再后的引退酒会,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的庞大客户群,爱泽艾米丽也仍创下了2天内收入2亿日元的高额流水记录。
这样的收入水平,完全能达到日本上流社会的水准。
更何况,身为高级“陪酒人”,爱泽艾米丽所付出的,不过也是俊俏的皮囊而已。
零付出,十收获——这样的致富之路,对日本女性的诱惑究竟有多大?
十九岁以下女性高达66%的涉足率,或许已经给了答案。
特别是在西方思想观念逐渐普及的现在,追求心灵和肉体的自由解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默契的共识。
第七次“青少年的性行动全国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女高中生有过性行为的比例就高达23.6%,50.8%的日本青少年认为,与异性在外过夜是“可以被允许的”。

这样的开放观念,无疑是催生风俗交易的最佳温床。
更何况,在如今的女性学生看来,在校期间埋头苦读勤恳求学,与离校后纵情红灯区的行为并不矛盾。
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风俗行业工作”视作再正常不过的课外兼职手段。
无论家境贫穷或是富有,自身能有余力给自己多挣一份零花钱,这样的机会,很少能有人视而不见。
甚至,为了能在潮流的风口浪尖傲视群雄,部分女学生还打起了风俗业的主意,利用这场“双赢”的选择来为自己谋取在同龄人中炫耀的KPI。
这样的比喻下,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学生群体会成为这部分灰色产业的主力军。
而另一边,家庭主妇的动机也与前者相差无几。
作为日本社会存在感最低的人群之一,家庭主妇的活动范围,被划定在自家厨房的一亩三分地上。
失去经济贡献能力、没有与年龄相匹配的职业幸福感,是大多数家庭主妇选择“下海”的主要原因。
与国内半躺平半内卷的社会现状不同,想要在社会资源本就告急的日本生存下去,男性就必须要承受更多的情绪压力。
世间万事都是守恒的。
为了维持自身状态的平衡,白天在公司作点头哈腰状的男性,下班回到家后,势必会将一天内的负面情绪无限倾斜到自己的妻子身上。

一旦被打上“无能”的标签,即使将家务事处理地面面俱到,女性也无法从“工作”中获取成就感。
如角田光代在《坡道上的家》中所塑造出来的,深陷“丧偶式育儿”困境的女主人公里沙子一样,无数聚焦日本家庭主妇情绪困境的文学作品,就是对这一现状的潜意识反抗。
在此基础下,选择依靠风俗业来为自己“正名”,多少也包含些身为家庭主妇的无奈之感。
而自奈良时期就存在的日本性文化,更是为家庭主妇的“出格”提供了精神依据。
脱胎于日本偏激的男尊女卑文化,家庭主妇眼中的风俗业,更多程度上带着一层无可厚非的即视感——
男人挣钱养家,灵魂和肉体都同样疲惫,那在外面逢场作戏,又错在哪里了呢?
既然不以风俗为耻,而且政府也默认发展,那看似“没什么用”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不能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价值”呢?
这样的道德观念下,男人流连,女人“下海”,已然成为了大众约定俗成的社会默契。

就连一直在试图扭转自己“性产业规制国”印象的日本政府,也在来回拉扯中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管吧,民众的反抗太剧烈;不管吧,整个国家都陷进了风俗的怪圈里。
索性各退一步,象征性管管得了。
1999年后,日本再次更改风俗业从业规范,将没有店铺的“私娼”划入合法范围、取消了风俗店的营业时间限制。
这一系列前后矛盾的动作,仿佛给日本政府蒙上了一层略显无奈的喜剧色彩。
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掌管全国命脉的日本政府,真的在民众舆论的汪洋中“覆舟”了?
其实,仔细琢磨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真相,远不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日本:成也风俗败也风俗
即使是最荒诞的艺术,也是对现实的无情投射。
这句话用在日本略显矛盾的风俗业上,看起来再适合不过。
在大部分国人眼里,风俗业是走投无路下才会选择的所谓“下等”行业。
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也曾在作品《月牙儿》中,用母女二人相继沦为暗娼的行文来讥讽时下环境的黑暗腐朽。
但在日本,之于国家经济发展,风俗业却意外的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就曾对日本风俗业的年营业额收入进行过汇总统计,得出来的数据让人瞠目结舌。
600亿欧元。这样的高额数据,即使放在西方各个发达国家,也是不容小觑的盈利趋向。

在日本,这样的年营业额,更是直接占到了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
打个比方,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我们总需要在水泥混凝土里加入钢筋结构,确保它不会在恶劣天气内被风吹倒,必要时还能容纳更多人挤进来避险。
风俗业,就是日本在经济下行时期所特有的“避风港”。
虽听上去略微有些不伦不类,但很显然,风俗业这一另类的“避风港”,在日本拥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
按照正常的投入产出节奏,想要依靠一项产业“养老”,势必要在前期倾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看管,直到它可以完全成熟,进入自动盈利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技术条件有多么成熟,一些无法避免的原材料投入总是必要的。
但对于风俗业来说,前期的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在还未成熟的奈良时代,不被允许的私娼照样可以赚得盆钵体满。
换句话来讲,通过依靠风俗业的疯狂盈利来带动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是日本近乎以零换十的超值交换。
这并不是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因式推导。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乘着国际经济局势的东风,日本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小国到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汽车出口国的华丽转变,每年的经济增速高达10%。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到2000年,这种状态下的日本,完全可以实现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即将出现的超级强国》中的预判,“成为经济第一大国”。
但就目前的形式来看,直到今天,预判仍旧还是预判。
原因也很简单。
那个年代,除去日本,近乎整个国际社会都处于虚假的“泡沫繁荣”里。一旦泡沫崩裂,飘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惨。
高速发展如日本,自然也跌入了楼市、股市双崩的惨剧中。
有一点不同的是,在“泡沫经济”下愈加繁荣的风俗业,在最后关头替国家扛住了持续亏损局面。
90年代初期,日本风俗从业者的平均薪资高达每天五万日元,相当于其他行业的月收入。
日本的陪酒文化规定,从业者的收入,按照顾客消费额的10%支取,政府则从中收取5%的消费税。
如此一来,日本的风俗业,无疑成为了拉起困境中日本的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后续日本仍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缓解泡沫崩裂对自己的负面伤害,但风俗业的存在感,仍旧一战成名。
正是由此,一直试图消解风俗业的日本政府,才会在后期宣布放宽政策,与“风俗”和谐共处。
这是日本深陷风俗业的首要原因。
而剩下的另一半,就要问问日本国内的男性同志了。
即使对日本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从动漫作品等文化输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的家庭结构,似乎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上有老下有小,去上班还要去捧老板的臭脚——日本点头哈腰的文化传统下,藏着男性同志数不清的抓狂瞬间。
既不能对老板发火,家里“赋闲”的妻子又听不懂自己的忧虑,怎么才能缓解内心的压抑?
索性去喝花酒吧。

为了能让男性同志第二天上班时,能够有足够充沛的精力为国家贡献生产力,夜晚的消遣活动就必须要跟上节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时代的更新迭代,日本没办法痛下杀手,大刀阔斧停顿风俗业,原因就在于大面积的民众诉求。
利用风俗业带飞其他行业不需要成本,可关停风俗业,面临的就是国内生产力的双重崩溃。
日本的政府官员,不至于算不清这样一笔简单的账面。
存在即是合理。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国内态度暧昧的风俗业,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的重要文化名片也就见怪不怪了。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帮助日本躲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但风俗业的从业者,依旧面临着来自政府部门的偏见。
最近的疫情风暴中,在为各行各业发放失业补助金时,风俗业就被有意无意的从名单中除名。
或许是因为从业者们“日进斗金”无需补助,又或许是长时间博弈下官方自尊心的死而复燃。
对于那些试图从此行业中找回自我归属感的从业者而言,这样的区别对待,值得细细品味。
参考资料
书剑为酒.日本人拘谨刻板 为什么他们的色情业却这么发达?[J].东西南北,2017(05):70-71.
萨苏.日本如何扫黄 日本警察和站街女的战争[J].世界博览,2013(20):16-18.
盘点世界各地坐台女[J].章回小说(中旬刊.专题版),2011(03):72-77.
王伟.日本AV女优的辛酸泪[J].文史博览,2010(05):64-65.
李敏.关于日本的风俗业[J].外国问题研究,2014(04):52-58.DOI:10.16225/j.cnki.wgwtyj.2014.04.009.
肖军.禁止下的规制:性产业在日本的法律境遇[J].时代法学,2007(06):92-98.
一牧,季华.歌舞伎町 霓虹中的欲望迷宫[J].城市地理,2020(09):108-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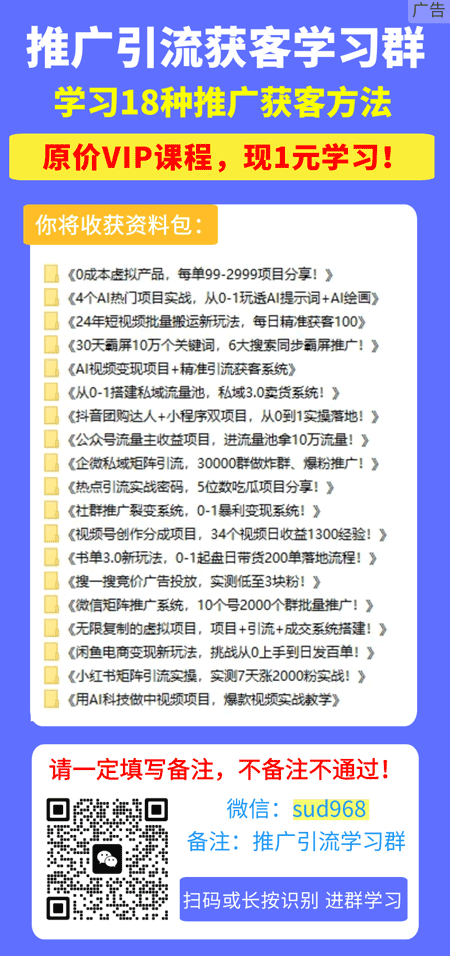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vsaren.net/11678.html